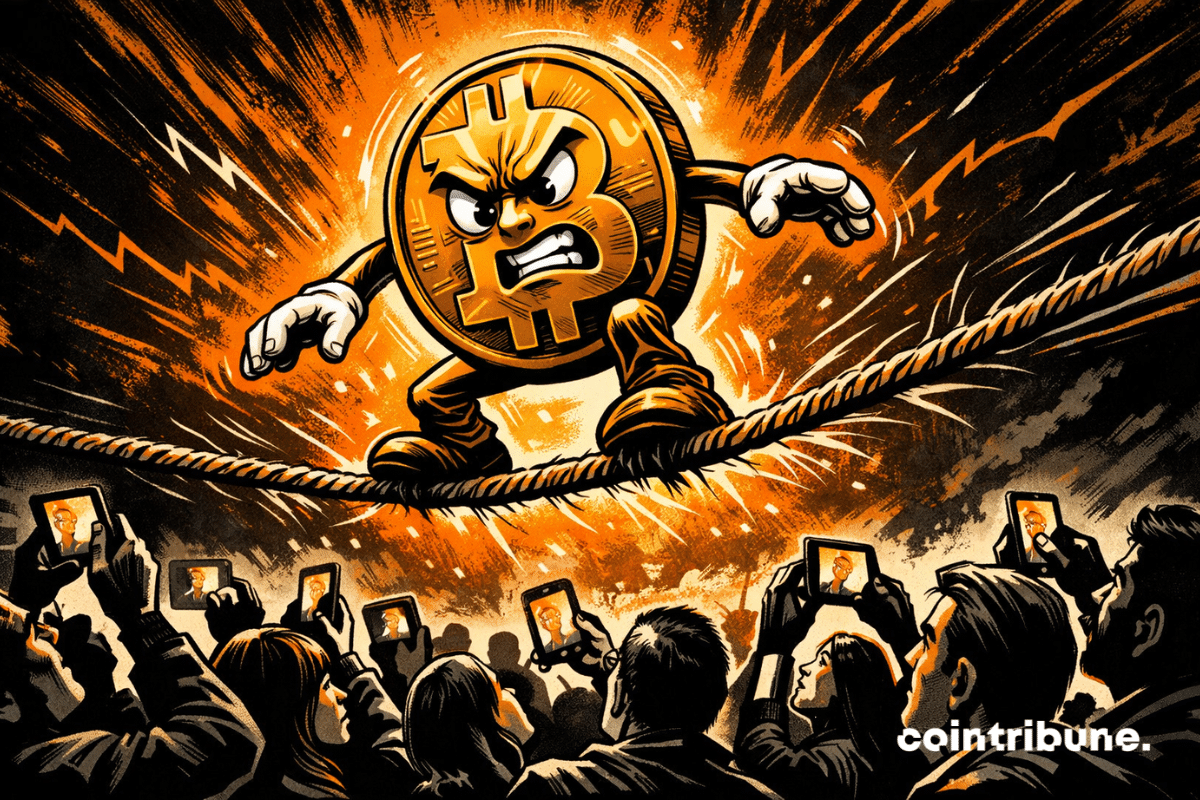特朗普世界最新的仓促判断伤害了我们所有人
作者:Brian O'Neill,佐治亚理工学院国际事务实践教授。
2026年1月,联邦移民探员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独立遭遇中杀害了Renée Good和Alex Pretti。
在Pretti被杀后不久,国土安全部部长Kristi Noem表示他犯下了"国内恐怖主义行为"。
Noem对Good也作出了同样的指控。
但"国内恐怖主义"这个标签并非Noem所指控的那种带有政治色彩暴力行为的通用同义词。美国法律将这个词描述为一个特定概念:危害人类生命的行为,似乎意图恐吓平民、施压政府政策或通过极端手段影响政府行为。意图是关键。
根据我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反恐中心管理反恐分析师的经验,我知道恐怖主义标签——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是只有在评估意图和背景后才能作出的判断。在调查开始之前不应使用。恐怖主义的认定需要分析纪律,而非速度。
证据先于结论
在第一个新闻周期中,调查人员可能了解所发生事件的粗略细节:谁开火、谁死亡以及大致发生了什么。他们通常无法以足够的信心了解动机,从而宣布存在胁迫意图——这一要素将恐怖主义与其他严重犯罪区分开来。
向国会提供政策分析的国会研究服务处提出了一个相关观点:虽然"国内恐怖主义"一词在法规中有定义,但它本身并非独立的联邦罪行。这就是为什么公众对该词的使用可能超越法律和调查现实的部分原因。
这种动态——在证据支持之前急于确定叙述的诱惑——最近在国土安全部部长的断言中可见,呼应了情报学术和正式分析标准中长期存在的见解。
情报研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观察:分析师和机构面临固有的不确定性,因为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模糊的,并且容易受到欺骗。
作为回应,美国情报界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将分析标准编纂成文。这些标准强调客观性、独立于政治影响,以及严格阐述不确定性。目标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通过严谨的方法和透明的假设来界定它。
当叙述超越证据时
当领导人在能够解释支持该结论的证据之前就公开称某一事件为"国内恐怖主义"时,恐怖主义标签就变得有风险。这样做会引发两个可预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一旦高级官员以绝对确定性宣布某事,系统就会感受到压力——有时是微妙的,有时是公开的——来验证这一标题。
在高调事件中,相反的反应,即制度性谨慎,很容易被视为逃避——这种压力可能导致过早的公开声明。调查人员、分析师和传播者可能发现自己在为上级的故事情节辩护,而不是从问题开始——"我们知道什么?""什么证据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是公众信任。研究发现,"恐怖分子"标签本身就塑造了受众如何感知威胁和评估回应,而不仅仅是基本事实。一旦公众开始将该词视为政治讯息工具,他们可能会贬低该词的未来使用——包括在胁迫意图确实存在的情况下。
一旦官员和评论员在评估意图和背景之前就公开承诺某个版本,确认偏差——将证据解释为证实自己现有信念——和锚定效应——严重依赖先前存在的信息——都可能影响内部决策和公众反应。
误用的长期代价
这不仅仅是专家之间的语义争论。大多数人对"恐怖主义"的心理档案是由大规模暴力和明确的意识形态针对性塑造的。
当美国人听到"恐怖主义"一词时,他们可能会想到9/11、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或海外的高调袭击,例如2005年伦敦爆炸案和2025年12月在悉尼的反犹太主义袭击,其中意图是明确的。
相比之下,更常见的美国暴力经历——枪击、袭击和与执法部门的混乱对抗——通常被调查人员视为、并被公众理解为杀人或针对性暴力,直到动机确定为止。这种公众习惯反映了一个常识性的顺序:首先确定发生了什么,然后决定为什么,然后决定如何分类。
美国联邦机构已发布了国内恐怖主义的标准定义和追踪术语,但高级官员的公开声明可能超越调查现实。
明尼阿波利斯案件说明了损害发生的速度有多快:早期报道和文件材料迅速偏离了官方说法。这引发了指控,认为叙述是被塑造的,结论是在调查人员收集基本事实之前作出的。
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后来与最初的国内恐怖主义声明保持距离,但更正很少能像原始断言那样传播得广泛。标签会留下,公众只能争论政治而非证据。
这一切都不会减轻针对官员的暴力的严重性,或事件最终可能符合恐怖主义定义的可能性。
重点在于纪律。如果当局有胁迫意图的证据——这一要素使"恐怖主义"与众不同——那么他们最好说出来并展示可以负责任地展示的内容。如果没有,他们可以用普通的调查语言描述事件,让事实成熟。
在事实之前使用"国内恐怖主义"标签不仅仅是在一个案件中冒着错误的风险。它逐案教导公众将该词视为宣传而非诊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一类别在国家最需要清晰的时候变得不那么有用。
您可能也会喜欢

CoinGecko 趋势数据显示抛售期间注意力集中在哪里

BTC/JPY在日本"铁娘子"高市早苗获胜后飙升